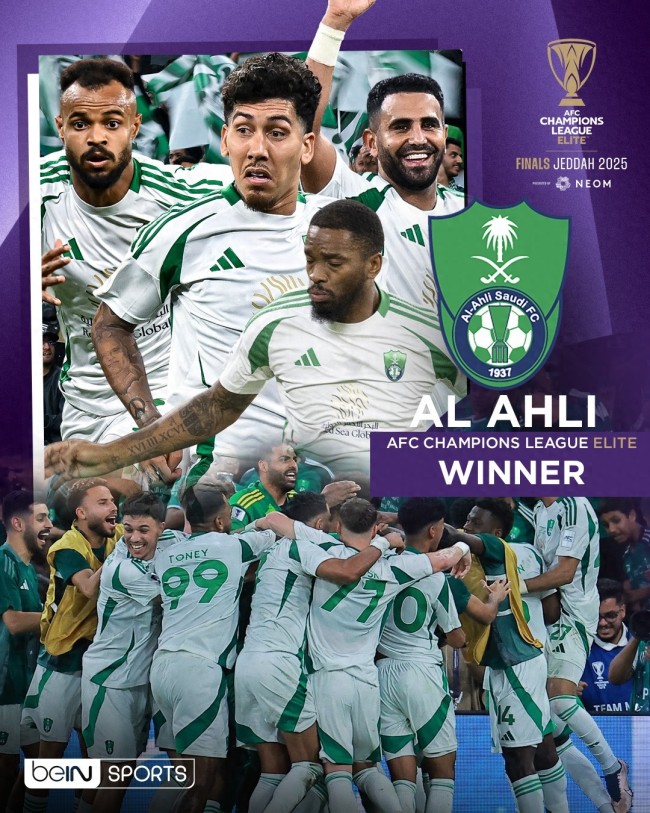马斯克回应“参选时间”:明年
当地时间2025年7月5日,马斯克在社交媒体宣布“美国党”成立,面对网友关于参选时间的追问,他以“明年”作答。这一表态不仅延续了其自6月30日以来与特朗普政府“大而美”法案的激烈对抗,更暴露出美国政治生态中技术精英与传统权力结构的深层冲突。
核心立论:马斯克的“参选时间表”本质是技术寡头对传统政党体制的解构实验,其背后是硅谷资本与华盛顿权力的权力再分配博弈。
从直接诱因看,马斯克的“造党”行动是对特朗普政策转向的直接反击。6月30日,他公开抨击特朗普力推的“大而美”税收和支出法案,称其将“让美国因浪费和贪污破产”,并威胁若法案通过将立即成立新党。7月4日法案签署前,马斯克发起网络投票,124.9万网民中65.4%支持建党,这一民意基础成为其行动的合法性注脚。这种“民意绑架政策”的模式,打破了传统政党通过党内协商妥协的决策逻辑,将技术平台的即时反馈机制转化为政治动员工具。
更深层的矛盾在于技术精英对政治话语权的争夺。马斯克虽在2024年大选中全力支持特朗普,但其“政府效率部”负责人的角色却暴露出双重困境:一方面,特斯拉董事会因政治参与导致股价波动,投资者强烈要求其回归商业;另一方面,特朗普政府内部对其削减20%联邦预算的激进改革方案抵触强烈。这种“商业利益受损”与“政治理想受挫”的双重挤压,迫使马斯克选择第三条道路——通过建立新党重构政治游戏规则。数据显示,2025年4月马斯克在威斯康星州最高法院竞选投入2300万美元失败,已证明传统政治捐款模式的低效性,而“美国党”的社交媒体动员模式(单条推文获百万级互动)则展现出技术赋能下的政治参与新可能。
然而,马斯克的实验面临三重悖论:其一,法律程序障碍。根据美国联邦选举委员会规定,新政党需召开党团会议、选举官员并完成州级认证,而马斯克至今未启动相关程序,其“明年参选”的承诺可能沦为政治表演;其二,意识形态模糊性。尽管马斯克批判两党“浪费贪污”,但其“美国党”尚未提出具体政策纲领,仅靠反建制情绪难以凝聚选民;其三,资本与民主的张力。马斯克个人净资产达4000亿美元,若以超级富豪身份组建政党,将加剧美国政治“金钱化”争议——2024年大选中,科技行业政治捐款已占总额的28%,新党的出现可能进一步扭曲选举公平性。
从国际视角观察,马斯克的行动与德国选择党、法国“国民联盟”等极右翼势力的崛起形成呼应。2024年12月,马斯克公开支持德国选择党主席魏德尔竞选总理,被德国政府指责“干预选举”。这种跨国政治投机,暴露出技术寡头试图通过输出“反建制”叙事重构全球政治版图的野心。但德国联邦议院选举中,选择党仅获18.5%选票,证明反体制情绪的转化率存在天花板。
马斯克的“参选时间表”更像是一面棱镜,折射出美国政治的深层危机:当技术资本可以随意“开关”政党、左右政策时,民主制度的代议制本质正在被解构。若“美国党”真的在2026年参选,其最大历史意义或许不在于赢得多少席位,而在于迫使传统政党重新思考:在算法与资本主导的时代,如何重建与民众的真实连接。这场实验的结局尚未可知,但可以确定的是,美国政治的“后两党时代”已拉开帷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