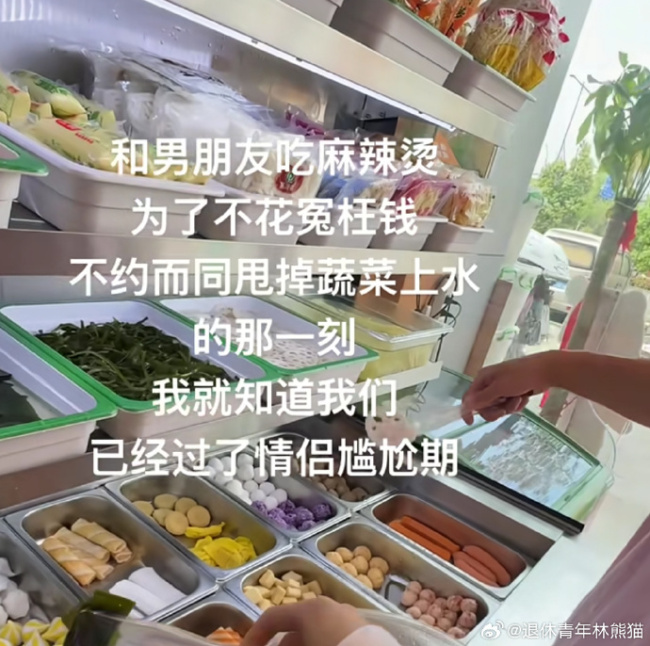李某某事件是隐含荡妇羞辱的厌女
当大连工业大学学生李某某因“与外国人不正当交往”被拟开除学籍的公告与“死亡证明书”谣言交织时,这场持续半年多的舆论风暴早已超越个体事件,暴露出社会对女性道德规训的深层逻辑——以“荡妇羞辱”为工具的厌女情结,正通过制度性压迫、舆论审判与性别暴力完成对女性身体的全面控制。
立论点:制度性羞辱与舆论审判构成双重压迫,本质是厌女情结的权力展演
大连工业大学对李某某的处分公告中,“与外国人不正当交往”的表述与《大连工业大学学生违纪处分规定》第十九条第六款“有损国格、校誉”的条款形成互文,将女性私人情感关系上升至国家荣誉层面。这种逻辑与2013年李某某轮奸案中辩护律师试图通过“受害人自愿”为其脱罪的策略如出一辙——均通过否定女性主体性,将女性降格为承载道德污名的客体。更值得警惕的是,学校在处分公告中公开李某某完整姓名,而涉事外籍男性Zeus的姓名却未被披露,这种“选择性隐私保护”暴露出制度对女性更严苛的道德审视。当Zeus仅以“没意识到她有男友”轻描淡写道歉时,李某某却面临学籍开除与社会性死亡,这种差异印证了厌女情结的核心:女性必须为男性的欲望与错误承担全部代价。
分论点一:荡妇羞辱是厌女情结的制度化表达,通过规训女性身体维护父权秩序
从南昌李某雪因“性格孤僻”被强制医疗,到西安财经大学学生李某某直播羞辱女生,再到大连工业大学对李某某的处分,这些事件共同构成一条隐秘的规训链条:女性身体始终处于被监视、被评判、被惩罚的状态。社会学家李银河指出,荡妇羞辱的本质是“通过污名化女性性自主权,维护男性对性资源的垄断”。大连工业大学处分规定中“与外国人不正当交往”的模糊表述,正是这种垄断思维的体现——将女性视为需要被“保护”的国格符号,而非具有独立人格的个体。这种规训在江西南昌李某雪事件中达到极端:当她因精神障碍表现出“异常行为”时,社区工作人员每日上门监视,邻居被迫搬离,最终通过强制医疗实现身体禁锢。这种对“非规范女性”的清除机制,与历史上对“疯女人”的囚禁一脉相承,都是父权秩序维护自身纯洁性的手段。
分论点二:舆论审判中的性别暴力,通过解构女性受害者身份完成二次伤害
在李某某事件中,网络谣言的传播轨迹清晰展现舆论如何参与荡妇羞辱:从Zeus粉丝群泄露亲密视频,到网友人肉出李某某身份,再到“死亡证明书”谣言引发“她活该”的嘲讽,每一步都遵循“受害者有罪论”的逻辑。这种审判与2013年李某某轮奸案中辩护律师曝光受害人杨某隐私信息的策略高度相似——通过暴露女性私人生活细节,削弱其作为受害者的可信度。更危险的是,这种审判往往披着“道德卫士”的外衣:当网友指责李某某“有男友还与外国人交往”时,他们实质是在复述“好女孩不该有性欲望”的父权教条。斯坦福大学性别研究显示,遭遇荡妇羞辱的女性中,63%会出现抑郁症状,41%产生自杀念头,而社会对这种伤害的漠视,恰恰印证了厌女情结的普遍性。
反论点:制度与舆论的双重压迫是出于对“国格”的保护,与性别无关?
部分观点认为,对李某某的处分是基于“维护国家形象”的公共利益考量,而非针对女性。但这种辩解忽视了两个关键事实:其一,涉事外籍男性Zeus的姓名未被公开,处分公告仅针对李某某,说明“国格”在此仅是规训女性的工具;其二,类似事件中男性极少成为道德审判对象——2024年长沙雨花区女干部李某某不雅聊天记录事件中,官方虽对其免职立案,但舆论焦点更多集中在“权力寻租”而非道德批判,与对女性事件的审判强度形成鲜明对比。这种差异暴露出厌女情结的隐蔽性:它总是以“公共利益”“道德规范”等中性词汇为掩护,实质却是对女性自由的系统性压制。
驳论:女性自主选择交往对象是个人权利,不应被道德绑架
针对“与外国人不正当交往”的指责,需明确:成年女性有权自主选择交往对象,这是基本人权。联合国《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明确规定,女性应享有与男性平等的个人自由选择权。大连工业大学将私人情感关系定义为“有损国格”,不仅违反国际公约,也与我国《妇女权益保障法》中“国家保障妇女享有与男子平等的人身权利”的规定相悖。更讽刺的是,当Zeus辩称“我们只是普通生活记录”时,社会选择相信加害者的“无辜”,却对受害者施加更严苛的道德审查,这种双重标准正是厌女情结的典型表现。
深层洞察:破解荡妇羞辱需构建“女性主体性”保护体系
要终结这种压迫,需从法律、教育、舆论三方面入手:法律层面,应明确禁止“荡妇羞辱”行为,如法国2022年通过的《反街头骚扰法》将言语羞辱女性定为犯罪;教育层面,需将性别平等纳入中小学必修课程,参考瑞典“无性别教育”模式,消除对女性的刻板印象;舆论层面,应建立“受害者保护机制”,如韩国2021年实施的《性犯罪处罚特例法》修正案,禁止公开受害者信息。当西安财经大学学生李某某因羞辱女性被留校察看时,学校若能借此开展性别平等教育,而非仅停留于处分,或许能避免更多类似事件发生。
从大连到南昌,从校园到网络,荡妇羞辱的阴影始终笼罩着中国女性。当李某某的“死亡证明书”谣言与处分公告共同构成一场荒诞的道德审判时,我们看到的不仅是制度对个体的压迫,更是一个社会对女性自由的恐惧。唯有承认女性是具有完整人格的主体,而非承载道德污名的客体,才能终结这场持续千年的规训游戏——毕竟,一个允许女性自由爱的社会,才配谈文明与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