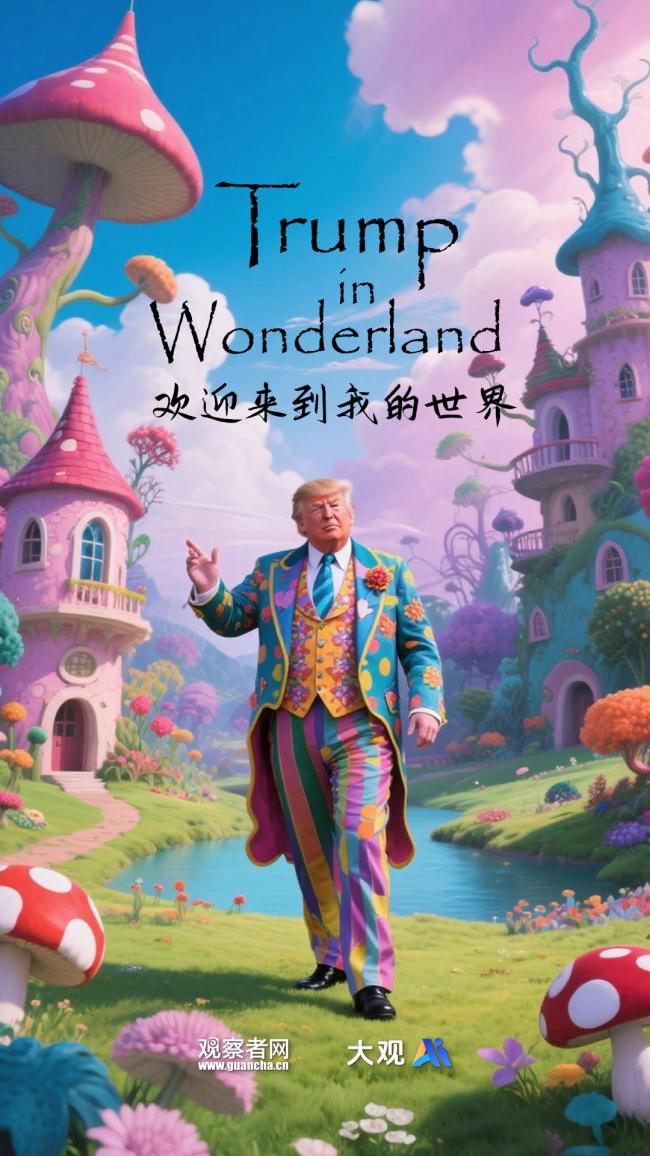女子2.5亿存款失踪 银行:储户有过错
2025年7月15日,“工行南宁分行2.5亿存款失踪案”在南宁市青秀区人民法院开庭,银行方仍坚持“储户有过错”的抗辩立场。这场持续数年的金融纠纷,不仅暴露出个别银行内控体系的系统性溃败,更折射出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机制的深层缺陷。
立论点:银行内控失效与储户风险意识缺失的双重困境,本质是金融机构责任让渡与消费者保护失衡的必然结果。
分论点一:银行内控失效是案件核心诱因,银保监11次预警印证系统性失守
涉案员工梁某红作为工行南宁分行个人金融业务部总经理,利用职务便利伪造存单、调包客户身份证,在银行VIP室完成资金盗取。更令人震惊的是,银保监部门曾连续11次向工行发出风险提示,指出其存在“大额存单异常支取”“同一代理人多次代理资金流向异常”等问题,但工行未采取有效拦截措施。这种从员工行为排查到系统预警的全面失效,远非“个人犯罪”所能概括。根据《商业银行法》第六条,商业银行有义务保障存款人合法权益不受任何单位和个人侵犯,而工行南宁分行在风险预警后仍放任操作,已构成对法定安全保障义务的实质性违反。
分论点二:储户“过错”认定存在法律逻辑悖论,高息诱惑不构成责任自担的充分条件
银行方强调储户因追求2%额外利息而“通过非正规程序操作”,试图援引山西清徐农商行案中“储户担责八成”的先例。但该案与本案存在本质差异:清徐案中储户主动将身份证和存单交予员工代办,而本案中梁某红利用工行高管身份,在营业场所内以“企业方核验身份”为由骗取证件,储户全程处于被诱导状态。最高法(2021)最高法民申1928号裁判观点明确指出,储户预先收取利息不构成存款合同项下过错,银行不能仅以“高息揽储”为由免除自身责任。工行将2.5亿存款损失简单归咎于储户“贪利”,实质是转移矛盾焦点,逃避监管责任。
反论点:银行“技术中立”辩护难以成立,营业场所安全义务不可推卸
工行代理律师在庭审中提交9组证据,强调“存单背面已风险提示”“操作流程合规”,试图以“技术中立”原则撇清关系。然而,梁某红作案过程中,其助手时某持储户身份证进入柜台后仅2-3分钟即完成转账,暴露出银行对代理取款业务的身份核验流于形式。根据《储蓄管理条例》第二十九条,银行对代理取款负有实质审查义务,而工行南宁分行允许非授权人员短时间内完成大额资金划转,已构成对法定义务的严重违反。银保监局2020年对工行广西分行罚款150万元的处罚决定,亦从监管层面印证了银行存在“异常资金支付业务核查不到位”的过错。
驳论:将“职务侵占”偷换为“盗窃”的司法定性,不能成为银行免责的挡箭牌
本案争议焦点在于梁某红行为定性:若构成职务侵占,银行需承担赔偿责任;若定性为盗窃,则储户只能向犯罪人追偿。南宁中院一审判决将梁某红行为认定为盗窃,但储户代理律师指出,梁某红利用工行高管身份、在营业场所内、通过银行系统完成资金转移,符合“利用职务便利”的职务侵占特征。更关键的是,即便按盗窃论处,根据《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九十八条,银行作为经营场所管理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造成他人损害的,仍需承担相应责任。工行以“刑事定性”规避民事赔偿,是对法律逻辑的刻意扭曲。
前瞻性观点:重构金融消费者保护体系需打破“银行绝对强势”格局
此案暴露出我国金融消费者保护机制的三大短板:一是银行内控监督形同虚设,二是司法裁判标准模糊,三是储户举证能力薄弱。建议从三方面改革:其一,强制银行建立“异常交易双录追溯”机制,对大额资金变动保留全程影像证据;其二,明确储蓄合同纠纷中银行“安全保障义务”的司法认定标准,禁止以“技术中立”规避责任;其三,赋予金融监管部门对消费者集体诉讼的公益支持权,降低储户维权成本。
当2.5亿存款在银行监管下“不翼而飞”,当11次预警沦为一纸空文,这场荒诞剧的终点不应是储户血本无归。金融机构必须明白:每一次对安全义务的懈怠,都是在透支整个行业的信用根基。唯有以制度刚性约束权力任性,方能重建公众对金融体系的信任。